人在学术的大环境下,一定会受到积极的影响,但有时也受负面影响,甚至是阻碍。叶嘉莹先生那一辈的部分学者亦有过从这些负面影响和阻碍中突围的经历,这些既帮助他们完成学术上的辉煌,也带来不少非议,其实都正常不过。我无意歌颂,也无意辩护,只想以词学为例,看看叶先生如何从两种负面影响和一种阻碍中突围,完成其学术使命。或许,这是客观评价她学术的一个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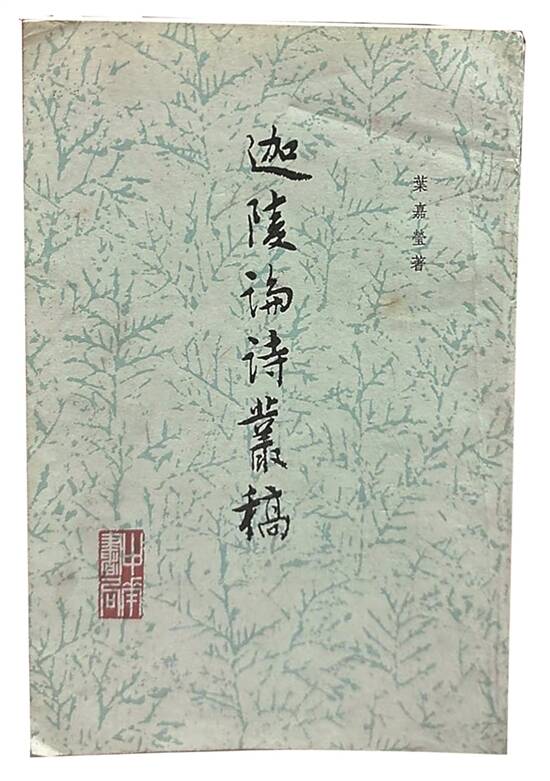
《迦陵论诗丛稿》,叶嘉莹著,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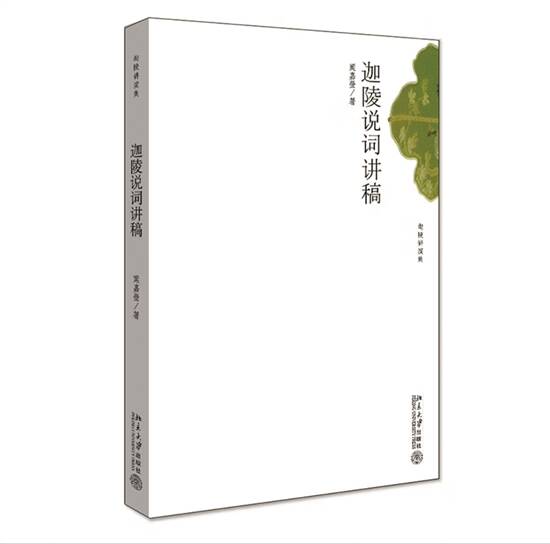
《迦陵说词讲稿》,叶嘉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壹
那一辈学者没有选择,初涉学术就被裹挟进一个特殊环境。时代矫枉过正地反对传统,如同婴儿跟着洗澡水被一起泼掉。词学在这大环境中处境极为不利。我认为常州派是词学发展的巅峰,但他们的主旨和采取的策略都已无法被时代理解。张惠言的策略是,将“《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选序》),比附于艳体小词。这实在是个很不讨好的方式,封建道德统帅美学正是时代所猛烈抨击的。其实张惠言却有极大的洞见。艳体小词处在社会道德的最边缘,不像《诗经》的恋歌可以附着在社会伦理关系上,似乎孤悬在人伦之外。由之传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词选序》),就和道德的功利性划开了几乎所有的关联。于是摆落一切政治功能的无功利道德突显了,文艺因此具有了哲学性,儒家诗教的真实意义同时展现。这是儒学探求了千余年未曾达到的目标,难怪谭献对此兴奋莫名:“向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复堂词话》)可在那个时代,儒学不是要被痛打的落水狗吗?更加不利的是,深受常州派影响的晚清词学,遗老色彩太重,妥妥成了已陈刍狗。一位年轻作者的词话渐受追捧,其批评了常州派、蔑视了晚清诸家,再加上拿来了西洋理论,尽管就词学来说我认为其专业性有待商榷,但和当时的学术环境水乳交融。这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坦率说,《人间词话》对以“思索安排”(叶先生论周邦彦词的说法)为基本艺术法则的南宋慢词,无法理解。王国维自己说:“北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词辨》批语)晚清诸家无不重视南宋慢词,以之为专业性的表率,王国维如此直言近于挑衅。在《人间词话》里,这种态度隐藏在那个著名的“隔”字背后:“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人间词话》)为什么敢于把自己的不专业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这仍是时代矫枉过正地反对传统在他身上的一个体现。另外,这个态度倒是更倾向常州派。“思索安排”的法则过于偏重形式,容易沦为“游词”(这是常州派的金应珪在《词选后序》里对南宋慢词一脉末流的批评术语),于是丧失了词的内在品质。张惠言重视这种品质,王国维同样重视。但他们依赖的思想资源不同,张惠言取之于儒学,王国维取之于西洋哲学。从王国维的《论性》《释理》两文中,可见他对儒学缺乏真正的理解。但他并不从内容上攻击,而是利用了张惠言一个显见的表述缺陷。这个缺陷便是仍以政治化功利化的语言表述超越了政治化功利化的道德,从而导致重陷旧局。但张惠言实在很无奈,毕竟首次面临一个新问题,他没能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后来的常州派词学家表示了理解,陈廷焯“规模虽隘,门墙自高”(《白雨斋词话》卷一)的说法可谓持平。王国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深文罗织”(《人间词话》)这样激烈的指责,实在说不上“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其实,张惠言的缺陷早已为常州派自己弥补,这就是周济作出的贡献,他改变了那种政治化功利化的表述方式。周济的表述很睿智:“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样把两面都保住了,“有寄托”肯定了张惠言强调的内在品质,“无寄托”开启了超越功利性的新表述方式。王国维自己没法表述得如此完美,有意无意地沿袭了周济。
但沿袭的不过是方法,内容却不相同。王国维的词学理论集中表现在“境界”说里,不过“境界”说本身非常驳杂,容纳了很多未能统一的因素。其中有三层含义值得注意。第一层大概原本是主要的,但王国维似乎并不很重视。这就是他借用严羽“兴趣”说指出的那种美,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过严羽意指的是盛唐人包含了这种美的一个更丰富的美学现象,王士禛的“神韵”说则单纯只指这种美了。所以王士禛比严羽显得狭隘,他欣赏的并非全部盛唐而主要是王维。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美学“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做了学理的阐释,既比严羽明晰,也比王士禛全面。他还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人间词话》)而王士禛只认识到景物。可以说,这种美虽并不陌生,但王国维借助德国古典美学资源完成了明确的学理阐述,功不可没。不过,既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人间词话》),这种美毕竟占据不了词中最上的位置,王国维仍需继续深入。于是在他最喜爱的叔本华的独特哲学中找到了比那种美更终极的东西,成为“境界”的第二层含义。王国维走得很远,直达叔本华哲学的最深处:“意志的整个现象取消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它们的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都取消了。没有意志,也就没有表象,没有世界。于是留在我们之前的,怎么说也只是无(德语:Nichts)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王国维对无功利道德从无体认,却对无功利审美别具会心,这个“无”正是带着消极意味的纯粹审美心理,被他一眼觑定。当然也是后来虚无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符合王国维的时代大环境,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最钟爱的“境界”。李煜的词境最符合这层含义,因此在《人间词话》中得到最高评价,就完全不难理解了。“境界”的第三层含义,比如评论李璟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晏殊、柳永、辛弃疾词为“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人间词话》)则可看作是对周济词学有意无意地沿袭,或说让步。本来这一层和前两层并非同类的审美概念,不过在“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点上一致而已。但做出这点儿让步,就给“境界”说留下更大的被接受空间,其实非常关键。但“无”成为终极性之所在,而非道德,这毕竟是王国维的主要内容,因此哲学上终欠一层,也就理解不了张惠言的深度。康德将美作为向善的过渡,常州派与之一致,即使以西洋哲学来衡量,王国维也落在下风。
叶先生那代人初涉词学,很少不受《人间词话》的影响,顾随先生如此,她也如此。只是顾先生才力太足,突围而出得那么简劲利落,叶先生则迟疑彷徨了许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已经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潮,还是如此评价王国维和张惠言:“王氏之说词乃是属于对美学客体的一种哲学诠释,而张氏之说词则是对于美学客体的一种政治诠释及道德诠释。”(《迦陵随笔》六)这就是我说的学术大环境的负面影响。但从她对“境界”说的关注看,不难发现她集中在“境界”说的第三层含义,这实在是王国维对周济的沿袭。我跟随叶先生读书时,先生特别爱问新生一个问题:“王国维指责张惠言‘固哉皋文之为词也’,但自己又用三种境界去讲晏殊他们的词,这是为什么?”我理解她一边问着学生,一边自己反思着,试图利用周济走出王国维。先生从王国维的歧路进入词学,最终突围出来走向正轨,周济作为王国维词学的一个罅隙,给了突围的便利。从先生的学术经历看,她对常州派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肯定。她后期著名的“弱德之美”的提法,实际是常州派和王国维词学的完美结合,算得她创造性的贡献。这是先生从第一种负面影响中的学术突围,即使看起来没有新的建树,但扭转了百年学术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值得被高估的。
贰
叶先生面临的第二种学术大环境,负面影响小很多,她的突围也简劲利落。甚至可以说,给了她更多有利的积极影响。那是上世纪60年代,先生前往北美任教,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新的文艺思潮从海外风行到大陆。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后来回到中国,具有学术敏感的她自然必须应对,何况又早得风气之先。因此,她一直被看作以中西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给她带来很大的声誉。但我并不认为她在这方面的努力值得被高估,一来这对她也是个全新的挑战,那些形形色色的新理论她没有精力做出彻底的理解,毕竟她无意成为文艺学的专家;二来现代文艺思潮偏重方法,往往忽视终极性的大问题,精致有余格局却促狭,比起叔本华都远远不及。因此对于这些思潮,只可利用来作枝节上的小修补,却不宜全盘移用。叶先生对此一直是清醒的,但她的读者却未必,他们震慑于西方的学术霸权强势,对那些理论津津赞叹。如此看待先生这方面的研究,真令人有买椟还珠之叹,可看作一种负面的影响。先生很快感到这个负面影响,作出策略性改变,毅然甩脱西方理论的生硬外壳,将之化入中国固有的理论中。温庭筠和韦庄,作为常州派最推崇的作者,并不太受王国维青睐,先生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以“双重性别”和“双重语境”说论证了常州派的合理性。“双重性别”说提出较早,利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痕迹较显,她引用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斯·利普金《弃妇与诗歌传统》(1988年)的观点,认为“男女两性因地位与心态不同,故男子难于自言其挫辱被弃,乃使得男性诗人不得不假借女性之口以抒写其失意之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三纲”中君臣和男女之间具有对应关系,逐臣和弃妇的伦理地位与感情心态之间往往自然构成呼应,“所以利普金氏所提出的男性诗人内心中所隐含的‘弃妇’之心态,遂在中国旧社会的特殊伦理关系中,形成了诗歌中以弃妇或思妇为主题而却饱含象喻之潜能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但在提出“双重语境”说的时候,她将诠释学理论和周济词学做了完美结合,指出“南唐之词与西蜀之词原来确实有一种共同的美感特质,那就是其词作之佳者,往往在其表面所写的相思怨别之情以外,还同时蕴含有大时代之世变的一种忧惧与哀伤之感”。(《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词学家对此种特质之反思与世变之关系》)这不仅是周济“词史”论的一个现代理论的翻版,而且全文没有一处来自西方理论的直接引文,直是化境。长期的学术训练,让先生迅速从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的负面环境中突围而出,她得鱼忘筌地使用着那些方法,使词学完成了和现代西方理论的对话,这才是应该被高估的。
叶先生学术声望愈隆之际,却遭到当代大陆学界一部分学者强劲的阻碍势力,这也并不难理解。中国当代过度推崇乾嘉考据式的学术,并从历史学领域转向哲学、文学领域,逐渐显出不利的趋势。本应高扬人的主观精神的文学,沦为以实证方法爬梳文学材料,以绝对客观态度考据文学思想,为己之学终为稻粱之谋取代。叶先生的学术框架既已定格,面对这样的学术生态,便很少再有交集。这种生态并不理解她,当然也不理解常州派、王国维和西方的学术。互相之间本无对话,先生不过超然遗世而独立,有的人便剩下仇视和拒斥了。
经历了这些突围,她却未负时势,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词学百年的歧途、扬弃了现代西方文艺思潮、对抗着当下部分扭曲的学术生态。这,就是她的学术贡献。
阅读原文
作者丨钟锦(六后宝典资料大全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丨羊城晚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